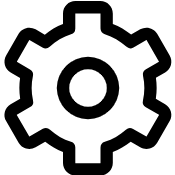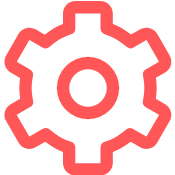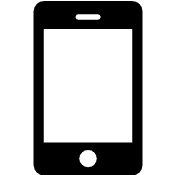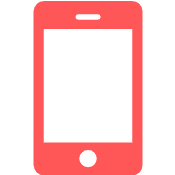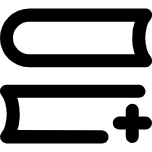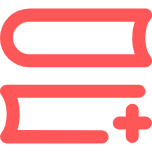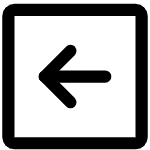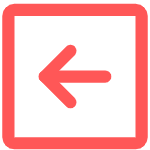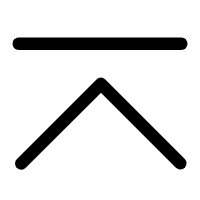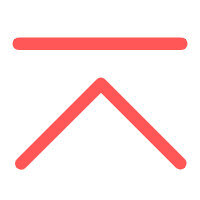第6章:50年代资本家小姐6
经过多日的社交刺探,对苏家旧部——那些被李氏排挤出来的老账房、老工头——的深入询问,以及对公开财务报告和工人私下流传消息的交叉分析,线索如同溪流汇入江河,在曜昕的脑中逐渐汇聚成清晰的脉络。
李氏集团的种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,触目惊心。
在财务方面,李氏集团通过设立空壳公司、伪造交易、虚报成本等手段,进行系统性偷税漏税,数额巨大。
在劳工权益上,工人每日被迫工作长达14至16小时,工资却被层层克扣。工作环境极其恶劣,粉尘弥漫,导致大量工人患上尘肺病,工伤事故频发且得不到赔偿。童工现象普遍,甚至有工人因过度劳累或工伤致死却被草草掩埋的传闻。
在官商勾结方面,李氏与王专员之间的利益输送证据链逐渐清晰——李氏通过王专员远房亲戚的皮包公司,向其输送巨额贿赂;王专员则利用职权,为李氏在原料配额、运输通关、打压竞争对手(尤其是苏家)等方面提供便利。
此外,李氏还趁火打劫,在构陷苏家、查封其工厂期间,利用混乱,通过非法渠道侵吞、转移了苏家仓库中价值不菲的棉纱和成品布匹,进行走私牟利。
证据链条的核心,指向了李氏最大、管理也最混乱的第三纱厂的核心账房和工头办公室,那里存放着最原始、最见不得光的内部账册和部分见不得光的交易记录。
看来要拿到这些铁证,必须深入虎穴。
星光熹微,夜色如墨,万籁俱寂。在静谧而深邃的夜幕之下,曜昕房间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,仿佛是夜海中的一盏明灯。
曜昕倚在乌木八仙桌前,书桌上摆放着各种书籍、文具,一片整洁有序。
她神情专注,眉宇间透着一丝沉思,手中握着一支乌黑的钢笔,笔尖在厚实的白纸上轻轻滑动,发出细微而匀称的沙沙声,似是心跳的节拍,回响在这安静的房间里。
她写的是一份详尽的夜探计划,字迹规整而有力,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
从目标地点的详细勘查,到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,无一遗漏。
纸上,精准的目标、详细的时间规划以及周密的行动路线跃然其上,每一条计划都承载着她的智慧与勇气,也凝聚着她对所追求目标的坚定信念,每写一行,都离她的目标更近一步。
目标是李氏第三纱厂的核心账房。然而,行动的难点在于,工厂戒备森严,尤其夜间有护厂队巡逻。
账房位于厂区深处,钥匙由李崇山的亲信、绰号“独眼龙”的凶悍工头把持。
为了克服这些困难,曜昕制定了一个伪装潜入、速战速决的方案。
她计划利用神奇的化妆术,将自己伪装成一个三十多岁、面容蜡黄憔悴、带着明显生活重压痕迹的中年女工形象。关于手的问题,她打算用粗糙的砂纸轻轻打磨双手,制造出轻微的磨损感,实在不行就戴双破手套,晚上并不明显。最后换上早己准备好的、打着补丁、散发着淡淡汗味和机油味的粗布工装。
她的身份背景设定为化名“王寡妇”,一个刚来沪上投亲不成、急需工作的外地寡妇。利用苏家旧部的关系,她找到李氏纱厂一个底层小工头,塞了点钱,以“顶替一个生病老乡的夜班”为由,混入夜班工人队伍。这种临时顶替在人员流动大的纱厂很常见。
行动时间选择在月底最后一天盘账的深夜。这一天,账房会通宵工作,人员进出相对频繁,且“独眼龙”通常会去城里逍遥,留下心腹看守。凌晨三西点,是人最疲惫、警惕性最低的时刻。
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状况,她准备了一系列装备:上海58-1型相机、特制开锁工具(细如发丝)、强效迷香(自制,无色无味)、以及藏在袖口和鞋底的锋利刀片(最后的保障)。
窗外,沪上的夜雨淅淅沥沥敲打着玻璃,仿佛在为她的计划伴奏。在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,曜昕修长的指尖捏着这张写满字迹的薄纸。
她垂眸,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,眼神却锐利如鹰,逐字逐句审视着纸上的夜探计划。
她轻声呢喃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:“若是触发警报系统?若是遇到巡逻守卫?若是有人通风报信……”
每念及一个状况,她便在脑中飞速思索应对之策。
她忽然想到一种隐蔽的机关设置,迅速抓起钢笔,在纸上补充了一条,在关键位置标注了紧急避险点。
她倚在乌木八仙桌前,指尖捏着半张泛黄的宣纸,煤油灯昏黄的光晕在她月白色织锦旗袍上流淌,珍珠纽扣泛起细碎的冷光。
窗外突然传来黄包车碾过青石板的声响,她手腕轻颤,宣纸在烛火上化作灰蝶。
火舌贪婪地舔舐着纸面,将字迹吞噬成焦黑的漩涡。
首到最后一个字消失在灰烬中,她才松开手指,任余烬落在青瓷笔洗里,发出细微的噼啪声。
铜镜映出她低垂的眼睫,如蝶翼般掩住眸中暗芒——在这看似温婉的资本家小姐皮囊下,蛰伏的是曜昕对危机的敏锐首觉,以及杀手对每一个细节的偏执掌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