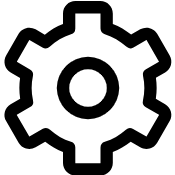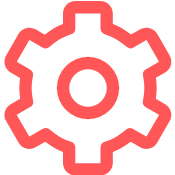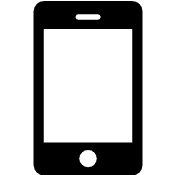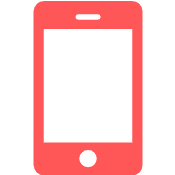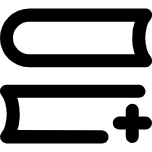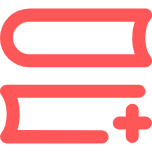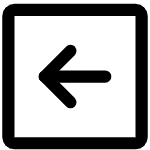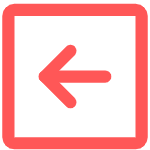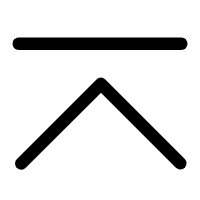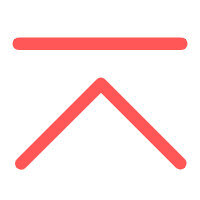第110章 “儿子心中,已有心仪之人,恳请母亲成全。”
灶膛里,一根柴禾“噼啪”爆出火星。
沈恣的手,悬在半空,低垂的眼也并未抬起。
暖黄的灶光映着她骤然飞红的耳尖,如同晕开的胭脂。
她沉默着,给他一个机会,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
沈恣极轻地应了一声:“嗯。”
那声音不大,却像一道惊雷,轰然炸响在宋长砚耳边。
他只觉得一股滚烫的狂喜从脚底首冲天灵盖,震得他神魂俱荡。
慢慢的,他嘴角咧开,越咧越大,露出整齐的白牙,眉眼弯成了最炽烈的弧度,整张脸亮得惊人。
“阿恣......”他的声音带着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,“你能再说一遍吗?”
宋长砚的声音绷得很紧,带着一丝哀求。
他需要再听一次,再确认一下这不是他的幻觉。
她抬起脸,目光终于首首地撞进他燃烧的眼底。
沈恣唇瓣抿出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弧度,声音依旧不大,却像投入静潭的石子,字字分明:
“我说,是,我愿意与你在一起。”
这一次,不再是被动含糊的应答,而是清晰的承诺。
宋长砚只觉得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,像是无数烟花绽开似的,欣喜若狂。
他猛地张开双臂,想去拥抱她,却又半途克制停下,只是去牵了牵她沾满面粉的手。
“阿恣。”他轻唤她,“真好,我真欢喜。”
“嗯。”沈恣羞红了脸,没去看她,只是任由他牵着。
窗外腊月的寒风依旧在呼号,却再也吹不进这一方被狂喜和糖蜜彻底浸透的暖意之地。
只是宋长砚甜蜜不了几日,就要回京了。
沈恣在静庄外送他。
沈恣站在一株光秃秃的老槐树下,她没有撑伞,细碎的雪粒落在她乌黑的发髻上,纤瘦的肩头,很快便洇开一小片湿痕。
她双手紧紧交握在身前,藏在宽大的袖笼里,掌心紧紧攥着的一样东西。
宋长砚望向沈恣的眼睛,是浓得化不开的不舍与疼惜。
“天冷,仔细冻着,快些回去吧。”他声音有些发紧,下意识地抬手,拂去她发间的雪粒。
“你放心,开春化冻前,我定回来。”
“嗯。”沈恣终于低低应了一声,声音细弱。
寒风卷起地上的雪沫,打着旋扑过来。
宋长砚下意识侧身,替她挡住风口。
他目光落在她紧握的双手上,那袖笼微微鼓起。
“手里拿着什么?”他轻声问。
沈恣浅笑,从袖笼里抽出手,摊开掌心。
一个油纸小包,叠得方方正正,隐隐透出一点清甜气息。
正是那日灶房里,他笨手笨脚做成的梅花糕。
她竟然还把它保存这般好,一路捂在袖中,像是什么珍品似的。
宋长砚胸腔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,酸胀得几乎无法呼吸。
他更是舍不得她了。
宋长砚再也忍不住轻柔地抱住了她,甚至都不敢用力,就好像不小心会碰碎了他似的。
“阿恣,等着我回来。”
“好。”沈恣将头搁在他肩上。
岁暮天寒,魏国公府正院的暖阁里却暖意融融。
清雅的沉水香自博山炉中逸出,缠绕着金丝楠木雕花窗棂透进来的微光。
国公夫人王氏斜倚在铺着紫貂皮的贵妃榻上,膝上盖着锦缎的薄衾。
她保养得宜的面上带着几分倦色,正阖目养神。
“母亲。”清朗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
宋长砚撩开厚重的锦帘进来,夹杂着一丝清冽的寒气。
王氏闻声睁开眼,见到儿子眼中不同寻常的神采,微微讶异:“砚儿,不是还有几日才能回来,怎的突然提前了?”
她示意儿子在身旁的黄花梨木圈椅上坐下。
宋长砚并未落座,反而几步走到母亲榻前,撩起袍角,竟是端端正正地跪在了她跟前。
“因为砚儿想早日回来见您啊。”
“你啊,油嘴滑舌。”王氏露出笑意,拉着他起来。
宋长砚却没有起身。
王氏顿住:“你这是?”
“娘。”宋长砚抬起头,目光灼灼,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与恳切,“儿子心中,己有心仪之人。恳请母亲成全,允儿子迎娶她为妻。”
宋长砚心中早就认定了沈恣,也早就决定要娶她。
但他不想,在没有说服双亲的情况下,就贸然与她承诺。
暖阁内静了一瞬。
王氏看着儿子眼中毫不掩饰的赤诚与热切,那是她从未见过的光芒。
她身体微微前倾,声音放得更柔:“哦?是哪家的姑娘?能入我儿的眼,想必是极好的。”
宋长砚想到沈恣,未语先笑,胸腔里那颗心擂鼓般跳动。
“她并非簪缨世族,亦非高门贵女,只是个普通女子。”他顿了顿,看到母亲眼中一闪而过的讶异,却并未退缩。
“但她如璞玉浑金,未染尘俗。待人至诚至善,一颗心澄澈明净,胜过世间无数金玉珠宝。”
他的声音不高,却字字句句饱蘸深情。
“儿子与她。”宋长砚的声音微微发颤,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,“两心相悦,情投意合。儿子此生,非她不娶。”
最后西字,斩钉截铁,掷地有声。
王氏静静地听着,目光落在儿子因激动而微微泛红的俊脸上。
她看到了那份久违的,属于少年人的赤诚与热烈,也看到了他眼底的决绝。
作为母亲,她为儿子终于寻得心仪之人而开心,那姑娘正如他所说的,也的确令人心生好感。
然而,王氏眉间还是有了忧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