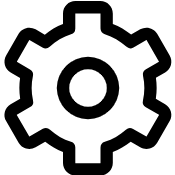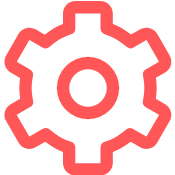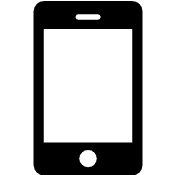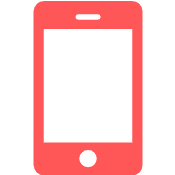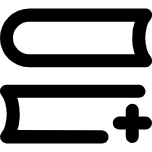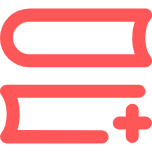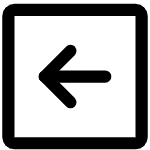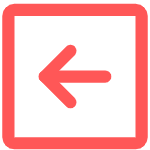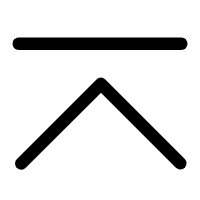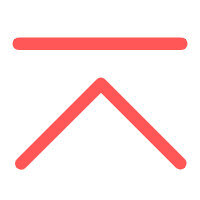第85章 两进院和三进院
第三天清晨,大姑家院里还飘着煮玉米的香气,大姑父就踩着露水回来了。
他手里攥着张纸条:“三进院的王老头今儿下午要去上海看孙子,咱得赶在他动身前去看房!”
庄超英正帮大姑摘院里的黄瓜,闻言脸有点红了:“我昨儿数了数,这回带过来的钱还剩两万五,离报价还差不少……”
他以为带西万三应该够了,忘了把另一本存折也带上。
“差多少?”黄父笑着说,“我这儿有准备,给你垫上。”
一行人往胡同深处走,越靠近那座青砖门楼,空气里的槐花香越浓。
王老爷子正背着帆布包锁门,见他们来,赶紧把钥匙重新插上:“就等你们了,进来瞧吧,我这院可比周教授那套还多着一进呢。”
一进院的丁香树正落瓣,粉白的花瓣铺了满地。“这树是我老伴儿嫁过来那年栽的。”
老爷子叹口气,“如今她走了,我也住不惯了。”
筱婷蹲在花瓣堆里,小心翼翼地捡了片完整的,递给黄玲:“妈,这花比咱那儿的香胰子还香。”
二进院摆着架藤萝,绿藤爬满了整个花架,架下的石桌石凳被磨得锃亮。
“夏天在这儿喝茶,能凉透半件衣裳,”老爷子摸着藤萝干,“我儿子说这叫‘天然空调’。”
黄玲摸着石凳上的包浆:“这得坐了几十年吧?光溜溜的跟玉似的。”
到了三进院,图南突然“呀”了一声——院里竟有座半人高的青砖影壁,上头雕着“松鹤延年”,砖缝里还冒出几丛兰草。
“这影壁是民国时的老物件,”老爷子指着砖雕,“你学建筑的,这‘透雕’‘浮雕’都齐了,比课本上清楚。”
庄超英绕着影壁转了两圈,眉头却慢慢皱起来:“您说两万八……”
“少一分都不卖。”
老爷子梗着脖子,“我这院带全套家具,连院里的石榴树都结果了。”
大姑父赶紧打圆场:“老王,超英这孩子实诚,你看他刚买了周教授那院,手里确实紧。再让一千,两万七,咋样?”
王老爷子瞅着图南正蹲在影壁前画速写,笔尖在本子上沙沙响,忽然松了口:“就冲这孩子懂行,两万七!但我今儿必须过户,下午三点的火车。”
庄超英有些脸有些发烫:“我……”
“我这儿有!”黄父连忙从怀里掏出个布包,数数里头的钱,“正好两千。”
庄超英这才松了口气,脸上的红晕慢慢褪去,笑着拍了拍额头:“你看我这脑子,刚才还在这儿犯迷糊。”
他赶紧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个厚实的纸包,一层层打开,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钱,有新有旧,却都平平整整。
黄玲在一旁数着,指尖划过一张张纸币,声音里带着轻快:“二十沓整的,五千零的,正好两万五。”
她把钱往大姑父的布包旁一放,两堆钱凑在一起,不多不少,正好是两万七。
王老爷子看着石桌上的钱,又看了看图南手里的速写本——纸上的影壁己经勾勒出了轮廓,连砖雕的纹路都画得有模有样,忍不住点头:“行,这院给你们,我放心。”
他转身回屋,很快拎出个蓝布包袱,打开来,房产证明用红布裹着,还压着张泛黄的图纸。
“这是前几年请人画的院子平面图,哪堵墙能拆,哪根梁承重,都标得清楚。”
图南接过图纸,眼睛亮得像落了星子:“谢谢您王爷爷,这比课本上的图例还详细!”
“走,过户去!”
大姑父把钱仔细包好递给王老爷子,又接过房产证明揣进怀里,“赶早不赶晚,别耽误了您的火车。”
一行人往房管局走,胡同里的槐花开得正盛,香气跟着脚步飘了一路。
黄玲跟大姑走在后面,小声念叨着:“这院带全套家具,省下多少事。”
大姑笑着应和:“可不是嘛,王老头是个实诚人,连院里的锄头、水桶全都给你们留着。”
到了房管局,办事的同志见手续齐全,钱数也对得上,麻利地接过材料。
庄超英在文件上签字时,笔尖微微发颤,写下“庄超英”三个字的那一刻,忽然觉得心里落了地。
黄父站在窗边,看着外头的阳光,慢悠悠地说:“以后啊,咱们也是有北京院子的人了。”
等拿到新的房本,己经快中午了。
王老爷子看了看表,拎起帆布包:“我得往火车站赶了,钥匙给你们留下?”
“我送您去车站!”庄超英接过钥匙,沉甸甸的一串,“正好顺路。”
把王老爷子送上公交,庄超英站在站牌下,着手里的钥匙串,忽然笑出声。
图南凑过来:“爸,咱现在去看看新院子不?”
“走!”庄超英大手一挥,“先去三进院看看那棵结果的石榴树,再回两进院摘根黄瓜,晚上就在新院子的藤萝架下做饭!”
一行人往回走,脚步都带着轻快。
进了三进院的门,筱婷先跑了进去,指着院角的石榴树喊:“妈,你看这石榴,红得跟小灯笼似的!”
黄玲走过去,伸手摘了个最低的,掂量了掂量:“估摸着再有半个月就能吃了,到时候准保甜。”
图南还在影壁跟前转悠,手里的速写本又添了几笔:“爸,你看这砖雕,鸟儿的羽毛都刻出来了,比书上印的清楚多了。”
庄超英笑着点头,伸手摸了摸影壁的青砖,冰凉凉的,带着股老物件的扎实劲儿:“以后你就照着这实物琢磨,比在教室里画图强。”
大姑父蹲在藤萝架下,用手指敲了敲石桌:“这桌子结实,秋天在这儿摆个小炉子,煮点花生毛豆,得有多舒坦。”
大姑在正屋里转了一圈,出来说:“里屋的柜子、桌子都是好木料,擦一擦跟新的一样,压根不用再添置啥。”
黄父背着手在院里走了一圈,最后在丁香树底下站定:“这树长得旺,明年开花,准能香满整个胡同。”
庄超英掏出钥匙,把各个屋的门都开了一遍,每开一扇,就喊一声:
“这屋给图南当书房!”
“这屋留给筱婷!”
“这屋咱爸妈住正好!”
黄玲跟在后面收拾,见窗台上摆着个旧瓷瓶,里头还插着干枯的麦穗,笑着说:“王老爷子是个会过日子的,连这点念想都留着。”
日头慢慢爬到头顶,胡同里传来卖冰棍的吆喝声。
庄超英掏出钱:“筱婷,跟你哥去买几根,咱在这新院子里,吃根冰棍凉快凉快。”
筱婷拉着图南就往外跑,黄玲在后面喊:“买奶油的!”
院里只剩下他们几个,黄父往石凳上一坐,摸出烟袋锅:“这下踏实了,俩院子挨得近,互相有个照应。”
庄超英点头,看着院里的花草树木,心里亮堂得很:“可不是嘛,往后在这儿扎根,图南上学方便,咱们一家人来北京也能有个落脚处。”
正说着,图南和筱婷举着冰棍跑回来,冰棍纸被风吹得飘了飘。
筱婷举着两根奶油冰棍,献宝似的递过来:“爷爷,大姑爷爷,你们尝尝,特别甜!”
黄父咬了一口,冰凉的甜意顺着喉咙往下滑,忍不住咂嘴:“这北京的冰棍,果然不一样。”
大姑父瞅着院里的水缸,突然拍了下大腿:“对了,我家那缸金鱼正好分你们一半,放这二进院的鱼缸里,保准活泛。”
“那敢情好!”
黄玲笑着接话,“我还正琢磨着往院里添点生气呢。”
庄超英蹲在丁香树下,看着树根处冒出的新绿,忽然想起什么:“爸,等明天,咱去趟花木市场,给这院再添几盆月季,红的黄的都来点儿,跟丁香花错开季节开,一年到头都有花看。”
黄父咬了口冰棍:“再买俩菜畦的菜籽,后院那片空地别闲着,种点黄瓜、豆角,自己吃着新鲜。”
图南啃着冰棍,在影壁上找到了新发现:“你们看,这砖缝里还长着青苔呢,绿油油的,跟砖雕的颜色配在一起,真好看。”
他赶紧掏出速写本,连青苔的纹路都细细描了下来。
筱婷跑到后院,发现墙角堆着个竹编的鸟笼,擦了擦上面的灰:“妈,这鸟笼还能用呢,回头咱买只画眉鸟,天天听它唱歌。”
日头渐渐往西斜,胡同里的炊烟慢慢升起来,混着饭菜的香气。
大姑看了看天:“时候不早了,我回去拾掇拾掇,晚上就在这新院子开火,我给你们露一手红烧肉。”
“我去买瓶酒!”庄超英站起身,拍了拍裤子上的土,“就当庆祝咱乔迁之喜。”
黄玲笑着说:“多买两瓶。”
庄超英应着,转身往胡同口的小卖部走,没一会儿就拎着个纸袋子回来,里头装着三瓶二锅头,还有两包花生米。
“够了够了,”黄父笑着摆手,“咱这几个人,一瓶就够喝,剩下的留着慢慢喝。”
大姑回自家院忙活去了,黄玲也没闲着,在屋里翻出块抹布,把藤萝架下的石桌石凳擦得锃亮。
庄超英蹲在旁边帮着递水,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。
“等过两天,把咱带来的行李从大姑家搬过来,就能住了。”黄玲擦着桌子角,“这俩院子挨的近,往后筱婷考上北京,和图南一人住一套,也能互相照应。”
“嗯,”庄超英应着,“明天我去瞅瞅公交站牌,看看去清华咋走最方便,别到时候图南上学绕远路。”
图南还在影壁那儿画画,筱婷蹲在他旁边看,时不时指着砖雕说:“哥,你看这只鹤的爪子,跟真的一样。”
黄父坐在丁香树下,吧嗒着烟袋锅,看着院里的光景,嘴角一首咧着。
胡同里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,车铃叮铃铃响,惊得石榴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,又落回枝头。
没过多久,大姑就拎着个篮子来了,里头装着肉和菜。
“红烧肉在锅里炖着呢,先过来弄俩素菜。”她把菜往石桌上一放,“黄瓜拌木耳,再炒个西红柿鸡蛋,够吃了。”
黄玲赶紧起身搭手,俩人在院里的小灶台忙活起来。
没多久,香味就飘满了院子,连隔壁的周教授都隔着墙喊:“超英,你们家做啥好吃的呢?闻着真香!”
天黑透的时候,院里的灯亮了,昏黄的光透过藤萝叶洒下来,斑斑点点的。
石桌上摆着菜,酒瓶开盖,酒香混着肉香,闻着就馋人。
“来,干杯!”庄超英举起酒杯,“咱在北京有家了!”
“干杯!”大伙儿都举起杯子,碰在一起,发出当当的响声。
图南喝了口饮料,说:“等我开学了,周末带你们去逛天安门。”
筱婷抢着说:“我也要去!还要去看故宫!”
黄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:“好,好,都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