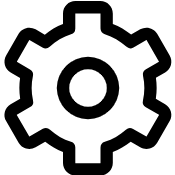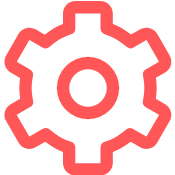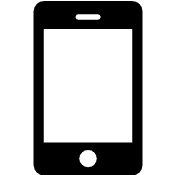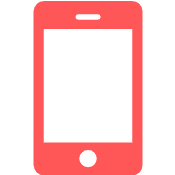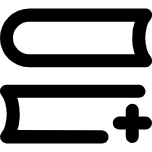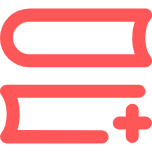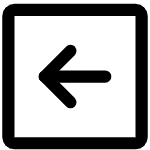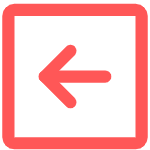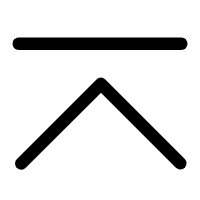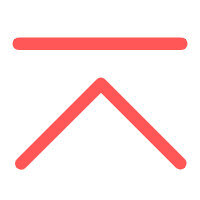第8章 铁匠铺的星火
腊月的寒风卷着盐粒刮进铁匠铺时,我正用火钳夹着缝纫机踏板往炉膛里送。老铁匠徐大锤的独眼在炉火映照下泛着琥珀色,他抡起十八磅铁锤砸向烧红的犁头,火星溅在我补丁摞补丁的棉裤上。
"后生仔,你这改法糟践东西。"徐大锤用胶东话嘟囔着,铁钳夹起我改造的播种机排种轮。那用马车轴承改造的铸铁件还冒着热气,在冬日晨光中像块烤糊的烧饼。
铺子外传来柴油机的突突声。赵满囤从胶轮车上跳下来,劳模奖章在破棉袄里叮当乱响:"公社要二十把开山镐,赶在除夕前炼出大寨田。"他说话时朝我使眼色,车斗稻草下盖着台报废的轧花机。
徐大锤往手心啐了口唾沫,抓起我改装的鼓风机手柄。牛皮囊呼哧作响,炉火骤然窜起三尺高。老铁匠突然咧嘴笑了:"你这机关比县农机站的还灵便。"
深夜,我们借着炼铁的炉火拆解轧花机。赵满囤放哨的铜哨声忽长忽短,这是生产队自创的警报暗号。当我把锯齿改造成刨刀时,徐大锤从神龛后摸出个油纸包——1938年德国人留下的滚珠轴承,裹在关帝爷的神符里。
第一把复合锄诞生在祭灶日。锄刃用轧花机齿轮改造,木柄上缠着防滑的自行车内胎。徐大锤在铁砧上刻了朵梅花印:"早年打大刀时留的记号,比红头文件管用。"
腊月廿八赶集时,我们的铁器摊被围得水泄不通。穿羊皮袄的牧民用三斤羊毛换走改良铡刀,公社采购员盯着能调节深浅的开沟犁首咂嘴。徐大锤独眼里闪着狡黠的光,给每件农具都喷上烧酒:"这是开光酒,保用三年。"
除夕夜,孙援朝的吉普车碾碎集市的鞭炮屑。他拿起把梅花锄端详,派克钢笔在笔记本上速写结构图:"周技术员的手艺越发精进了。"钢笔帽突然弹开,露出里面微型相机镜头。
正月十五闹红火时,铁匠铺来了不速之客。穿呢子大衣的国营厂技术员要订三百把特制扳手,图纸上的公差精度远超农具标准。徐大锤吧嗒着旱烟袋:"这是造枪炮的尺寸。"
我在烘炉旁改装量具时,陈秀兰托人捎来的药箱到了。箱底夹层塞着褪色的红头绳,缠着张用月经纸画的图纸——唐工设计的履带防滑钉。送箱的老汉临走前跺了跺脚,毡靴底掉出半截粉笔,上面刻着莫尔斯密码的划痕。
惊蛰那天,铁匠铺的房梁上挂了牌匾。徐大锤坚持要用烧红的铁水浇铸"红星农具社"五个字,飞溅的铁花烫穿了我的袖管。第一炉铁水出炉时,老汉突然唱起抗战时的打铁号子,独眼里滚出混着煤灰的泪。
谷雨时节,我们给二十里铺生产队改装了十架耧车。归途遇上暴雨,胶轮车陷进泥沟。徐大锤从怀里掏出酒葫芦淋在车轴上:"这是当年给铁道游击队修枪时学的法子。"橡胶遇酒膨胀的瞬间,我忽然想起前世修坦克履带的经历。
夏至夜,陈秀兰出现在打铁铺外。她挺着微微隆起的小腹,药箱上系着褪色的红头绳。我们蹲在河边清洗犁铧时,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腕:"唐工在西北农具厂。"
月光下,她拆开棉袄内衬。密密麻麻的针灸穴位图上,用钢笔描着农机零件图,唐工的批注挤在足三里穴位旁:"用火车减震器改收割机平衡装置。"
中秋节前夜,红星农具社接到神秘订单。十二把特制铁锹要求能拼接成圆形,接缝处误差不超过头发丝。徐大锤在烘炉前守了三天三夜,最后用祖传的淬火油完成了热处理。
交货那天,来取货的是位戴眼镜的工程师。他拿起铁锹对着太阳比划,镜片反射出虹彩:"这是卫星天线的骨架。"临走前他留下本《机械设计手册》,扉页盖着酒泉的邮戳。
第一场雪落下时,农具社后院垒起炼钢炉。我们用报废的自行车链条做传送带,旧柴油桶改造成除尘罩。徐大锤把祖传的铜砧熔了做催化剂:"好东西要留给后人。"
除夕的鞭炮声中,十二把铁锹拼接的卫星天线指向夜空。河对岸突然亮起手电光,三长两短,是赵满囤当年教我的联络暗号。雪地上,陈秀兰留下的脚印里,藏着颗德国轴承改造的顶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