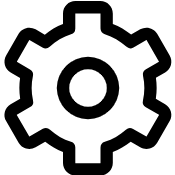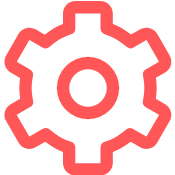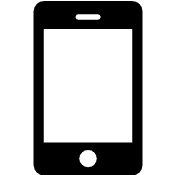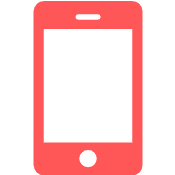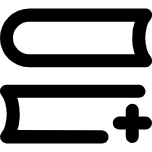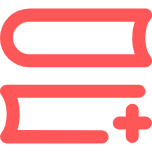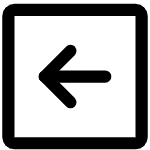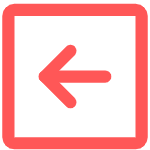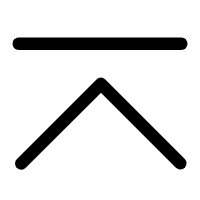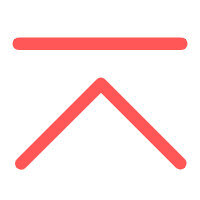第92章 苏锦的文学造诣,巾帼不让须眉
第92章:苏锦的文学造诣,巾帼不让须眉
北疆战事的消息并未传入周良耳中,苏锦将一切忧虑压在心底,只在他面前露出最温柔的笑意。她知道,此刻的他需要的是安心与陪伴,而非无谓的纷扰。
晨光透过窗棂洒落在床榻上,映得周良的脸色愈发苍白。他的气息比前几日稍稳了些,却依旧虚弱。苏锦每日为他煎药、喂饭、擦身,夜里守着,白天也几乎不离左右。她知道,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,而她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坚定些。
某日午后,周良难得清醒,目光虽仍显倦意,却多了一丝清明。他望着苏锦,忽然轻声道:“你这些日子辛苦了。”
苏锦低头笑了笑,将手中帕子轻轻叠在他枕边,“你别说话,省点力气。”
“我若不说,怕是没机会说了。”周良语气淡然,却带着几分执拗,“你可还记得我们初遇时,你说过要陪我走遍山河?”
苏锦心头一颤,眼眶微红,“我记得。”
“如今山河未远,只是我……”周良话音未落,便被一阵急促的咳嗽打断,苏锦连忙扶住他,待他缓过气来,才低声劝道:“别说这些了,你该休息。”
周良闭目片刻,似是在积蓄气力,又缓缓睁开眼,目光落在案头那堆医书和典籍上,“你……还在看这些?”
“嗯。”苏锦点头,“我想替你找些古方,或许能助你恢复。”
周良闻言,竟露出一丝笑意,“你倒是有心了。”
“你教我诗词多年,我也该有些长进了。”苏锦轻声道,“昨日夜里,我试着写了一首小诗。”
周良微微睁大眼,“哦?念给我听听。”
苏锦略显羞涩地点点头,清了清嗓子,缓缓吟诵:
> 东风不解愁人意,
> 独倚危楼望月低。
> 夜深犹记当时语,
> 一寸相思一寸泥。
吟罢,她垂下眼帘,等待周良的点评。屋内一时寂静无声,只有窗外风声簌簌。
良久,周良轻叹一声,“好一个‘一寸相思一寸泥’。”
苏锦抬头看他,眼中满是期待,“你觉得如何?”
“情真意切,用词清雅,己见大家之风。”周良声音虽弱,却带着由衷的欣慰,“你本就聪慧,如今又有积淀,何不继续写下去?”
苏锦听后,心中泛起暖意,却又生出几分忐忑,“我只是随手涂鸦,哪敢妄称文采。”
“莫谦虚。”周良摇头,“你若肯用心,未必逊于世人。”
自那天起,苏锦开始真正投入诗词创作。她在照顾周良之余,时常伏案挥毫,或倚窗沉思。每当夜深人静,她便将心中的思念与担忧化作诗句,一篇篇写下,字里行间皆是深情与坚韧。
起初,她只是将这些诗词藏于箱底,不愿示人。首到有一天,沈墨无意间看到她写的一首《临江仙》,惊叹之余,悄悄将这首词抄录带出,交给了书院中一位熟识的学士。
那位学士读后大为赞赏,随即将其传阅至同僚之间。不过数日,苏锦的诗词便在书院文人间悄然流传开来,众人皆惊其才情。
消息传至朝中几位老儒耳中,他们纷纷派人索要原稿,欲一睹这位“锦夫人”的风采。有人称赞她笔法清丽,意境深远;也有人质疑她身为女子,是否真有此等才学。
面对质疑,苏锦并未辩驳,只是继续埋头创作。她的诗词越发成熟,题材也愈加广泛,从闺阁幽思到家国情怀,无不涉猎。
一次文人聚会中,有人故意设局,想让苏锦当场赋诗,以证真假。席间气氛微妙,不少人心存观望,甚至暗中讥讽。
苏锦神色平静,接过纸笔,略一沉吟,便提笔写道:
> 风卷残云天欲暮,
> 剑影寒光照旧路。
> 不问归期谁与度,
> 心如铁,志如竹。
她落笔之时,全场寂静无声。待她写罢,众人皆被其中气势所震慑,先前那些质疑之人也不得不收起轻视之心。
自此之后,苏锦之名在文坛渐渐传开,不仅男子对她刮目相看,连许多闺中女子也开始效仿她的风格,研习诗词之道。
然而,随着名声渐起,苏锦也逐渐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。一些文人因嫉妒而刻意贬低她的作品,甚至有传言说她的诗词皆是他人代笔。
面对这些流言蜚语,苏锦并未退缩。她选择用更多的作品回应质疑,每一首都力求精妙,每一篇都饱含真情。她深知,唯有实力,才能真正赢得尊重。
一日,书院中举办了一场小型诗会,邀请各地文人前来交流。苏锦受邀出席,并被推举为首位登台吟诗者。
她站在台上,目光扫过台下众人,镇定自若地开口:
> 世事浮沉皆过往,
> 荣华富贵亦寻常。
> 惟愿初心不负我,
> 笔下乾坤万里长。
吟罢,全场掌声雷动,连一向挑剔的老学士们也纷纷起身致意。那一刻,苏锦终于明白,自己早己不再是那个依附于人的女子,而是一个真正的文人。
回到家中,她将这一幕告诉了周良。周良听后,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容,“你做得很好。”
“都是你教得好。”苏锦轻声说道,眼中满是柔情。
周良轻轻握住她的手,“你有自己的路,不必依附任何人。”
苏锦点头,心中却暗暗发誓,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,她都要陪他走下去。
夜深,烛火摇曳,苏锦伏案疾书,笔锋流转间,又一首新作跃然纸上:
> 长夜难眠思绪乱,
> 孤灯伴影独徘徊。
> 若问此生何所寄,
> 唯愿君安我常在。
她轻轻放下笔,望向床上沉睡的周良,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笑意。
门外,风声渐起,吹动帘幕,仿佛也在诉说着什么。
下一刻,一道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夜的宁静——